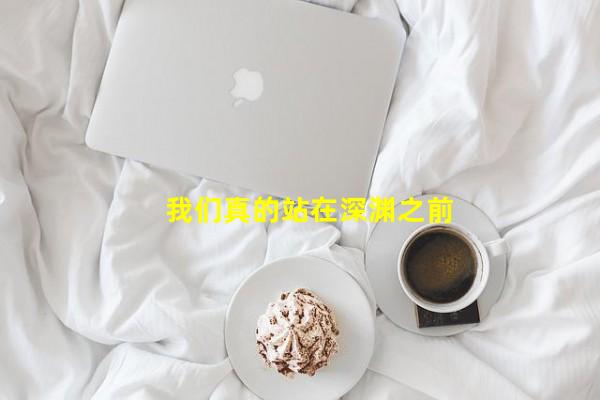
已故著名哲学家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曾任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师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与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
他有着扎根于柏拉图的古典学功底,亦卷入到整个现代性的争论中,透过对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反思与重构,探讨了虚无主义、分析哲学的内在困境。
《虚无主义》作者:(美)斯坦利·罗森 译者:马津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编者按:按照尼采的说法,虚无主义是一位站在现代社会门口的“最神秘的客人”,也应该是“最可怕的客人”。
斯坦利·罗森的《虚无主义:哲学反思》一书秉承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观点,在哲学思想的网格中绘制出虚无主义的历史脉络,不断回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理性主义,反思现代思想所面临的危机。
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学派,即主张现代性向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反对虚无主义和历史主义。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二者之间真正的哲学变革在于,古典时代的价值是奠基于地心说为代表的宇宙图景之上,事实与价值(自然与规范)贴合无间。
然而,日心说摧毁了这一宇宙图景,动摇了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并在牛顿的机械论宇宙图景中完成了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
这即是虚无主义的本质,尼采“上帝死了”的口号不过把既成事实表达了出来。
斯坦利·罗森的《虚无主义》一书就运用这一思路,把二十世纪两大哲学思潮现象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和分析哲学(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视为虚无主义的表现,因为他们都不再把自然看作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
本文是一篇以剧本对话形式写就的书评。
场景是夏炎与燕子君在图书馆中,谈论《虚无主义》一书涉及的关键主题。
罗森试图为古典立场提供辩护,而他的辩护是否成功却令人质疑。
于是,我们看到了夏炎与燕子君由此触发的一场论争。
存在的危机:殊途同归的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一个图书馆中)燕子君:你听说了吗?之前那个学弟决定去德国读海德格尔方向的哲学硕士了。
夏炎:哦?他不是很喜欢分析哲学吗?怎么转海德格尔了。
燕子君:据他说,是海德格尔而不是分析哲学让他在思想上能够回归生活。
夏炎: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分析哲学和欧陆传统相互的歧出和偏见很深,但总有人从这一头走向那一头,我一个老师翻译了海德格尔,然后转身去做维特根斯坦去了。
燕子君:其实,说不定他们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背景。
著名北美施特劳斯学派学人罗森在《虚无主义》中就意图探究他们背后的共同点。
夏炎:我知道一些。
罗森的野心不小,想把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看作是殊途同归的问题。
燕子君:是的,可以将其称之为,存在的危机。
夏炎:据我的印象,罗森把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看作是现代虚无主义的代表。
罗森是个施派,我知道施派的一个核心对话者就是海德格尔,他们把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挂钩。
可这就令人十分疑惑了。
历史主义认为所有事物都只有相对于历史语境的价值,没有普遍超越的价值,或为其他价值奠基。
说海德格尔把存在时间化历史化似乎并没有争议,但说维特根斯坦,尤其是早期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历史主义者,那就让人十分疑惑了,他不是一个“逻辑学家”吗?燕子君:让我们从头开始看看罗森对现代虚无主义的理解,你就会明白,罗森为什么会把维特根斯坦也视作虚无主义者,以及为何罗森认为,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背后的问题意识是一样的。
夏炎:愿闻其详。
燕子君:一说到“虚无主义”,我们就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著名论断,如果上帝死了,那就一切行为都被允许了。
这就是说,所有的行为,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标准,我们可以说它是善的,它是恶的,它是正确的,它是错误的。
在所谓科学的世代中,一个虚无主义者会坚定地相信,这些所谓的科学理论和理性精神,一方面断言了世界是什么,另一方面否定了过去,但同时期待着无法被表述的未来,也就是对价值的迷惑立场。
夏炎:这是罗森说的因主宰自然的计划从而引发的“存在的危机”?罗森在什么意义上说科学理性是一种虚无主义?而且,在康德那里,以及在胡塞尔、弗雷格那里,他们不都试图为我们的哲学寻找一个基础吗?这个基础是逻辑学的,虽然它们的逻辑学并不一样,但以逻辑主义反对心理主义上是一样的。
维特根斯坦不就是沿着弗雷格式的逻辑主义写作了《逻辑哲学论》吗?我们很容易从休谟式的心理主义里联想到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可逻辑主义不正是一种超历史的绝对的东西吗?起码我们容易这样想。
燕子君:可现代数理逻辑的基础又是什么呢?维特根斯坦在他书的最后,不就说“对于不可知的东西我们只能保持沉默”吗?那样一种现代理性的极端形态,一种数理逻辑,最后依托的难道不是一种特定的非理性吗?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早期时我们无法对逻辑形式进行言说,逻辑形式除了作为沉默的显现之外,几乎不再是任何东西,因而等于言说奠基于沉默之上,把理性奠基于非理性之上,实际上我们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而后期诉诸生活形式,而所谓生活形式不过是一种历史主义之下的“习惯”,“生活形式是历史的语言化身”,“就哲学而言,没有自然(physis),只有习俗(nomos)”,这是人在时间或在历史中创造意义的另一种表达。
言语基于沉默,正如理性依赖于非理性,这样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了,因为一切都是沉默。
虚无主义:居于不确定性之中夏炎:这样看来,虚无主义似乎是从“是”与“应当”分离开始的了,从自然与价值的分离开始了,“是”不过是一种存在,它不再标示任何价值了,一切都是沉默的显现,一切都是一样的,一切都被允许了。
燕子君:是的,用罗森自己的话说,“理性(reason)”与“善(good)”的分离。
也正是这种分离,使得现代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结成了隐秘的同盟。
这种分离,罗森的老师施特劳斯就已在其《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导言》中言及,这种现代理性的选择机制背后,其实没有任何真正可靠的基础。
而这就导致海德格尔重新发现了“存在”的危机以及存在作为一种显现的过程。
也正是因为这样,罗森认为,海德格尔会导向纳粹主义,虽然可能只是短暂的认同,也是有必然性的。
因为一旦纳粹被视为是存在的显现,我们又什么理由来拒绝它呢?夏炎:这真有趣,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历史主义者,我只相信所谓的价值不过是历史的沉淀和习惯,没有更深刻的基础,理性不过是工具而已,我们拒绝纳粹,仅仅是因为如果我们回顾整个历史,从我们长久以来信奉的价值,我们会觉得与其他方式相比,纳粹是更不能被接受的,我们只能居于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之中,不断在历史中保持平衡,我们失去了保证,我们只能自己艰难地前进。
顺便说一句,对于我这样的历史主义者而言,也没有末日,因为那也是一个绝对标准。
那罗森会怎么来面对这个困境?我知道施派喜欢讲柏拉图,可是柏拉图那一套在现代还行得通吗?他的理念论难道不就是一个神话吗?燕子君:罗森当然不会认为直接搬出柏拉图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的复古主义没有什么意义。
但他相信,我们能够从古典智慧中学到很多。
夏炎:学到很多,似乎很抽象,能不能展开一下。
毕竟,我们已经回归到存在的根基之前,不再受到沉默的限制。
燕子君:现代哲学,如黑格尔所言,因其存在的危机,故都转向了主体性的自由。
这一现象,阿里斯多芬在《云》中已经表现过:青年苏格拉底只会教导学生论证逻各斯(理性原则或本质),而非去决断公正。
我想施特劳斯并没有将海德格尔直接划入虚无主义的原因,正在于海德格尔尚能注意到希腊的原初性。
这一原初性所指向的,正是苏格拉底对于善的特征把握:善超越了一切可见事物的可能性,是“在场”与“所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