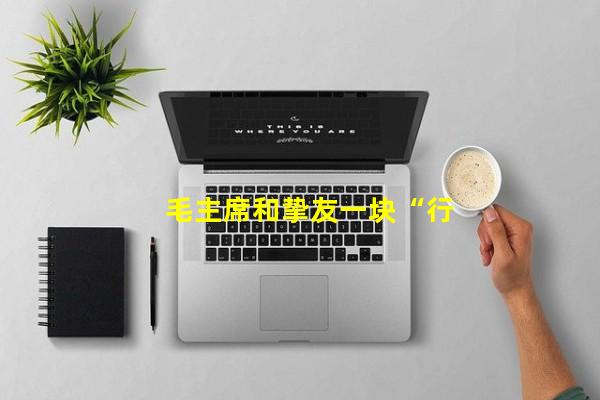
有一句老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沒有永远的敌人。
凡人如此,大人物也是如此。
毛主席与萧瑜友情一回,最后以分道扬镳收场,证实了友情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
人是变化的,包括友情,一对不分你我的朋友突然有一天要分手,这对彼此的伤害是巨大的。
毛主席与萧瑜的分手,不是凡夫俗辈之间因利益之争翻脸,他们的翻脸是因为主义之争,是信仰的分野,致使他们用青春热血浇灌起来的友谊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让人感到无限惋惜。
青年毛泽东一,萧家兄弟,对早期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与萧家兄弟的相识,是很早很早的,这要追溯到主席在东山小学读书的时候了。
那时,毛主席与萧瑜之弟萧三是同学。
萧家兄弟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是教书先生,有留洋经历,在当地或者省城都有名气。
萧三兄弟好读书,好谈论时世,这些爱好正与主席吻合,于是,主席便成为他们共同的朋友。
主席进东山小学读书时,萧瑜已经毕业到省城上学了,这段时间,毛主席对兄弟二人的友谊主要集中在萧三身上。
有一天,萧三从家里带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深深以及引了少年毛主席的目光:“这本书能借我看看吗?”“当然可以啦。
”萧三这本宣扬英雄人物的小册子,让这位来自湘潭的少年爱不释手,他利用几天的时间一口气把它读完。
书中的英雄人物有的是南征北战的开国之君,有的是开疆拓土的争霸雄主,如华盛顿,拿破仑,林肯,彼得大帝,叶卡捷林娜等等,都是毛主席十分钦佩的人物,他们建立的事功让少年主席读后为之震撼。
待他把这书还回去时,书页里划满了圈圈点点,写满了评注。
他对萧三说:“中国太需要这样的英雄人物了。
”东山小学毕业后,毛主席与萧三一起來到长沙。
后来,两人一起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而这时萧三之兄萧瑜已在一师就读三年了。
有一部电视剧里面说,毛主席考一师时,顺便为萧瑜兄弟写了两篇文章,于是三个人一起中榜。
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毛主席当年是为两个朋友代写了文章,但不是萧瑜兄弟。
这只能说明编导先生历史知识欠缺,或者为了情节需要张冠李戴,难道作为一师翘楚的萧瑜文章也写不了,还要找人代笔,岂不成了笑话?而且,毛主席当时也不是考的第一师范,是湖南第四师范。
在四师上了半年,然后四师与一师合并,毛主席遂成为一师的学生了。
毛主席与萧瑜的友谊正式开始。
两人都是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他俩与蔡和森并称“一师三杰”。
二、志同道合,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一九一四年,毛主席所在的四师与一师合并后,结识了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贵人杨昌济,同时与同是杨昌济的得意弟子萧瑜相熟。
两位热血青年都有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
他们都喜欢《新青年》这本新潮杂志,对经常在上面撰稿发文章的陈独秀和胡适非常钦佩。
作为《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同志是中国革命最早的宣传者,此时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还没有形成,但他对眼前这个旧世界非常憎恨,他用澎湃的激情呼唤新世界的到来。
萧瑜胡适先生是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宣扬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
他们的文章非常适合青年毛主席与萧瑜的胃口,因为他们对自己浸身于其中的世界也是憎恨的,竭力想改造它。
在一师读书的几年里,毛主席的思想与萧瑜大体一致,崇尚自由主义。
他们和当时大部分进步青年一样:反封建,反独裁,是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也是他们能够走在一起,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之原因。
三、了解社会,“行乞”游学中国是农业国,了解了农村,就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实。
非常人总是做非常之事。
主席认为,读了有字的书,更要读无字的书。
有时无字之书比有字之书更重要。
对农村的实地考察,是青年主席一直想做的事。
当时报上登了一则消息,说是两个学生徒步旅游中国,竟然走到西藏。
受之启发,毛主席也决定进行一次小范围的旅行。
毛主席的人生第一次社会考察,却以“行乞”的方式进行,这在常人看来难以理喻。
当时毛主席是个穷学生,而小他一岁的萧瑜师范毕业了,成为一个小学教员。
他们的身上没带一分钱,却成功地周游了长沙、宁乡、安化、 益阳、沅江五个县的很多乡村,结交上至县长下到雇工,还有乡绅,翰林,商店老板,寺院方丈等形形色色的社会各界朋友。
有时,他们还住在同学家里。
身无分文,身上的挎包里只能带着一把伞,和一些换洗的衣物。
山间人烟稀少,走几里才能看见个村庄,饿得晃晃悠悠的,必须讨点吃的才能维持体力。
在宁乡,他们“行乞”到刘翰林庄院,问明来意,年近七十的刘翰林给了他们四十个铜板,他们找了个饭馆,各用四个铜板饱餐一顿。
四十铜板很快花完了。
他们饿了只得沿村乞讨,有时看不到几家大户人家,只能到一些一般庄户人家,讨些冷饭剩菜,虽然半饥不饱,但也比饥肠辘辘强多了。
他们晚上的住宿一般在农户家里。
有一回,他们住在同学家里,这位同学家有钱,是财主,专门给他俩收拾出一间干净的屋子,主席却着意要他家的长工住一块。
晚上,他跟这位雇工亲切地聊天,收获了很多社会知识。
在宁乡沩山密印寺,他们一起会见了寺院方丈。
据萧瑜后来著文说,这方丈博古通今,是一位大学者。
他们究竟与方丈谈了什么,萧瑜也没有叙述。
后来,他们二人游学归来,毛主席曾给他的老师黎锦熙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这话的意思是,要改变当前的混乱局势,必须改变人心。
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必须找其本源在哪里。
沩山密印寺这时期,青年主席虽然没有接触马列主义,但他已经意识到推翻旧势力,必须找到一个统一或者武装人们思想的灵魂。
这个灵魂也就是信仰。
他们有时露宿野外。
青年主席总是充满浪漫主义情怀,他是这样评价他们的露宿的:大地当床,石头当枕,夜空当帐,月亮当灯。
后来主席回忆,在整个游学乞讨的过程中,萧瑜总是放不下架子,乞讨前总要整整衣冠,甚至干咳两声。
不过,他到乡绅家还能说几句,到普通农户家就退避三舍。
不像主席一开口就与这些农夫拉得很亲近,那种出自内心的真诚,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也许与主席出身农民有很大关系。
从行乞这件事上,也可以反映出主席以后联系群众的出色能力。
他们走到益阳县城时,感到情况与乡间大不一样,主席跑了两条街才讨到二十一文钱,于是他们决定卖字挣钱。
他们给一些商铺写字,写对联,赚了一些钱,解决了当日的饭钱。
一位茶店老板邀请他们喝茶。
原来,这老板也是读书人,只是为生活所迫,才做起买卖。
他有三个儿子,有两个儿子经商,另一个读书。
他叙述家事时,对自己的安排很满意:这样家传的读书之脉还能继续延伸下去。
茶老板得意的形态,让青年主席陷深思。
他对萧瑜说:中国人自私,家庭观念重,缺乏民族观念。
如果人人以国家为念,勇于献身国家,团结奋进,何惧列强的侵犯呢?!萧瑜说:“中国家庭就是家长制,国家也是放大的家长制,这是自由主义最大的障碍。
”从茶店出来,正准备到别处,突然他们看到一张告示上呈出县长的大名,这县长正是他们先前的化学老师张峰康。
他们决定见见张老师。
湖南益阳但门卫把两个行乞者进挡在门外,死活不让进,理由是如果把两个讨饭的人放进去,张县长会开除了他这个门卫。
主席与萧瑜一直在坚持。
没办法,门卫只得进去通报。
张县长会见了他们,并请他们共进晚餐。
第二天,派人把他们送到城外。
离开益阳,他们继续向沅江前行。
一路上,萧瑜对张县长品头评足,说张县长就是个势利小人,让门房挡住穷人不见,就是他的主意,这种人没有远大理想,一生就为权势活着。
青年主席沉默不语。
他正在思索着与方丈的交谈,心里在酝酿着如何救国民于水火中的策略。
总之,这次“游学”,为他以后在农民运动中的实地考察,打下了基础。
四、建也“新民学会”,散也“新民学会”“游学”后不久,青年主席从湖南一师毕业。
一九一八年四月,毛主席与萧瑜蔡和森等创办了新民学会,这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团体。
他们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确定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
所有的会员都思想进步,有着为国家民族做事的远大志向。
会员初期为二十多一人,后来发展到八十多人。
不久,从湖南一师调到北大教书的杨昌济给毛主席与蔡和森及萧瑜传来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三人便组织会员赴法留学。
新民学会会员他们认为,赴法可以了解西欧的工人运动及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革命有借鉴的作用。
为了学好法文,他们到北京进行短暂培训。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直接在李大钊手下效力。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者。
近水楼台先得月。
自此,胸怀大志的毛主席思想迅速得到转变,从一个无政府主义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与马列主义的深度接触,改变了青年主席去国勤工俭学的想法。
后来,他与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斯诺说: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从北京回来后,青年毛主席致力于《湘江评论》这张报纸的经营,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强调民众联合的力量, 并得到李大钊的声援。
文章号召人民大众联合起来,敢于斗争,争取胜利。
由于文章深刻揭示了民众的强大革命力量,引起反动统治者的恐慌。
1919年8月上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尚未发行就被反动军阀查封。
后来,毛主席又创办文化书店,通过书籍宣传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
书店办得很兴隆,很快就发展了七个分店,最后书店的命运也以查封告终。
在此期间,毛主席主持了数次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
毛主席一直与在法国的萧瑜保持联系。
萧瑜信仰自由主义,一直坚持教育救国的主张,反对暴力革命。
萧瑜从法国归来,一见面,两人各抒己见,为自己的信仰辩论。
萧瑜说,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他们的暴力在释迦摩尼看来,就像两个顽皮小孩打架。
毛主席知道他在暗示革命的暴力,于是便说,你不信奉马列主义,只能说是太遗憾了。
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新民学会会员也分成两派,一是以毛主席蔡和森为首的暴力革命派,其二是以萧瑜为首的温和派,主张改良社会。
赴法勤工俭学会员因为意见不统一,学会的宗旨不能一致,毛主席宣布新民学会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新民学会解散。
这也预示着两人关系的破裂。
而且,他们都为青春浇铸过的友情洒下分手的热泪。
后来,萧瑜全程陪同毛主席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一路上他们还在为各自的信仰争执。
毛主席全力争取萧瑜走到共产党这边来,但没有成功。
之后,他们的交往彻底断绝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毛主席一直忙于农民武装政权建设,一直忙于跟蒋介石打仗,无暇他顾。
直到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陕北时,他才与美国记者斯诺重新提起他这位昔日的老朋友。
“……和我一起旅游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
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
他给萧瑜谋到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
一一萧瑜盗卖了博物院的珍贵文物,然后卷款潜逃。
”毛主席说的一部分是事实,一部分并不是事实。
真实的事实是这样的:自与毛主席分手后,萧瑜进入了国民党政府工作,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
后随国民党跑到台湾。
还有一件事,是杨开慧被捕后萧瑜曾实施营救,这足以说明,萧瑜的人格是伟岸的,不是那种纠结于个人恩怨的小人,遗憾的是他的努力沒有成功。
后来,毛主席与诗人萧三谈起他的哥哥:“你们兄弟与鲁迅与周作人差不多。
”毛主席与萧三和小八路萧三说:“那我可不敢媲美。
”毛主席总结说:“就说兄弟关系这一点上。
”萧三比主席小三岁,也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二二年就加入共产党。
其时,身为共产党员的萧三已与投靠国民党的哥哥萧瑜决裂了。
但是,全国解放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席从直觉感觉到萧瑜的人品还是可以的,不相信他能堕落到私卖国宝卷款潜逃这一步。
在他的指示下,重新对萧瑜贩卖文物案进行调查,最后证明萧瑜是清白的,是他的所在的官场设计陷阱,对他的栽赃。
后来,毛主席再次说起萧瑜的时候,对他便是一种怀念的口吻了,并他人生的选择感到惋惜。
晚年萧瑜萧瑜厌恶国民党的官场,后来弃官到法国,后来又到南美的乌拉圭从事教育,台湾与大陆都不是适于他生存的地方。
他为了自由主义的信仰客死他乡,这也许是他最好的结局。
不过,他和毛主席一样,一生坚持自己的信仰,对他们早期的友情没有忘记,充满深情的怀念。
他曾写过一本专门记述与主席游学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伟大革命家形成前期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结尾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友情是想忘都忘不了的,因为他们彼此都有过真诚的付出。
毛主席与萧瑜的友谊就是这样。
是的,友谊珍贵,但信仰更宝贵,一生坚持自己信仰的人更令人敬畏!参考书:特里尔《毛泽东传》 ,斯诺《西行漫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