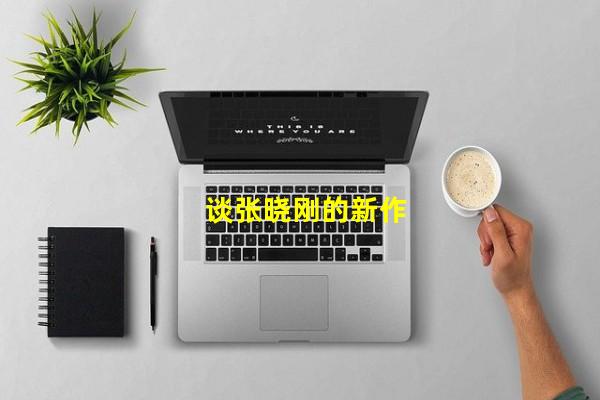
(文 / 崔灿灿)女性的肖像、吊灯、浴缸,是《镜子2号》里的全部形象;相连的椭圆形,倾斜的透视,露出一角的场景,将形象推向空间,某个含混的境地。
像画面里绿色的墙裙,那个景象对我颇为熟悉,也似曾相识。
这种场景在张晓刚新作展中极为普遍,你一定在生活中目睹过相似的情形。
张晓刚《镜子2号》,142 x 112 cm2018 ,纸本油画,纸张、棉线拼贴摄影:Guy Ben-Ari ©张晓刚张晓刚《镜子1号》 佩斯画廊纽约空间2018年9月7日至10月20日摄影:Guy Ben-Ari©张晓刚我常常在张晓刚的画作中看到自己曾经感受过的气息,可能源于1990年代或更早,某个公立医院的病房中,或是苏式建筑的办公室里下午3点的阳光,它从社会主义大街上照射而来;也可能来自我的知识经验,某个电影的镜头,如《雾中风景》里悬置在海面的雕塑,一只列宁的手臂;或是小说中描述的场景,卡夫卡笔下的某个房间,雷蒙德.卡佛写作的目光;或者只是相似,无法明确的辨析。
下午三点的光和1990年代一样的亲切,而又遥不可及。
无论何故,我对张晓刚的作品都有一种真切的想象:在我凝视画面时,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过去看到的一切,或是脑海中隐含的某个瞬间进行关联。
在众多真实反映中国政治图景的作品中,张晓刚的画作描绘了一个与现实有着差异的世界。
叙事性和文学性,个体的私密和悲观,成为他个人创作的显著风格。
以至于,我更愿意独自去观看他的个展,不同时期的作品构成的一个连续性时刻。
也只有在这个时刻,被政治图景遮蔽的意义才得以浮现:张晓刚的绘画超越了现实的存在,它将观者引入一个由阅读、感知、联想所主导的虚像空间。
在空间和虚像记忆的迁流中,我们熟悉那些画面中的眼神、动作或是场景,但又像是自己的眼神、动作和呆过的地方。
惊鸿一瞥之间,我们在镜子里开始阅读自己。
张晓刚《凳子上的人1号》,2018,纸本油画,纸张、棉绳拼贴,187 x 82 cm摄影:Guy Ben-Ari ©张晓刚张晓刚《床1号》,2018,纸本油画纸张拼贴,109 x 99 cm摄影:Guy Ben-Ari ©张晓刚一样的衣着,相似的表情,同样不知所起的光斑。
这是许多孩童,踩着凳子,望见的大人的世界。
《凳子上的人》描述了这个许多人有过的情形,我们曾经努力的接近成年人的视角,窥视高处衣柜里可藏匿秘密的角落。
偶尔,模仿照片的样子,举起锦旗,仪式般的敬礼。
但只是模拟动作,并不分享对于意义过多的期望和失落。
那时,我们还未成为社会的工具,未有阶级的区隔。
孩童有它自在的世界,就像列车驶过窗前,它并不关心一个孩子,某一时刻对它的努力张望。
一如张晓刚画面里的世界,从不回应我的凝视。
阅读是进入虚像世界的第一步。
我们辨识出一些基本的器物,悬挂的老式灯泡下,叠放着整齐的行军被,床边是一字排开的热水瓶和放在桌台的雕像。
原谅我在“物”之前堆砌的大量形容,它们的社会学意义早已被充分的解读。
我更感兴趣的是张晓刚所作的形容部分,它们被置于何种情形中,叙事又是如何展开。
感知成了第二步,长方形、椭圆形和混合而成的多边形,直接影响了观者对于形状的某种反应。
反复被运用的封闭性空间,四分之三视角的透视,暗示着作者观看的位置。
它为观众营造了进入叙事的路径,由画外向内延伸的结构,成了让观者进入空间的邀请。
张晓刚《浴缸》,2018,纸本油画,画报、棉线拼贴,144 x 203 cm摄影:Guy Ben-Ari ©张晓刚,佩斯画廊供图《自画像》 2016 《血缘:大家庭 No.2 》 1995但更多时候,“邀请”在张晓刚多数作品中,也包含了阻力。
一种两级的张力,始终徘徊。
一方面空间向外开放,邀请我们进入故事。
像是追忆的开始,吸引我们,重返过去的某个情形。
那一刻,感受孤立于现实之外;另一方面,他又让这个空间彻底封闭,没有门的墙壁、冰冷的背景从未提供出口。
它迫使观者停留,囚禁其中。
那一刻,观看的寂静有些孤单,进入冰冷的在场。
人们开始从静默如谜的温情中离开,身在别处,记忆远去。
不同的空间结构和叙事关系在张晓刚的绘画中反复出现,不断重复。
早期《大家庭》系列,端正的视角下,人物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
交错的个体之间,并没有留多少缝隙。
背景里,平面而又沉闷的灰色,有些压迫,一切喧闹和灰尘都被这弥漫着疑云的背景所笼罩 。
存在于这个空间之中的人,很难在这里找到归宿感。
相反,这个空间显得陌生、怪异。
漂浮的云朵挡住了所有天空的出口。
《蒙眼者之舞》 2016《贡品》 2016《重生1号:重生之门》 2016当空间区隔了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只剩下薄得可怜的墙壁和孤独的自己。
直到《失忆与记忆》系列,这个隐性的“墙”才变成了实体。
张晓刚为画面设计了复杂的空间,物像随之丰富起来。
平面的背景变成了立体的空间,平行的视角变成了四分之三侧视。
之后,广场、码头、大街、荒原,和囚笼式的狭小四壁,在张晓刚给予的目光中得以窥视,相互交替。
似乎,上一系列的困局在此得到解决,空间有了更多的选择。
然而,空间没那么容易被释解,在我们充分阅读和用力感受之后,这一切的努力仍是徒劳。
窗外不是美丽的风景,依然灰暗不已;无尽的地平线,总是被阻隔。
风景仿佛被施了魔法,成为另一个阴郁的异乡人,显得沉重而忧心忡忡。
《理想者》 2016《阅读者》 2016过渡、短暂、偶然便是现代性的所有本质。
没有点亮的灯,成了一个曲径,它将释解画面中的许多秘密。
光是空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