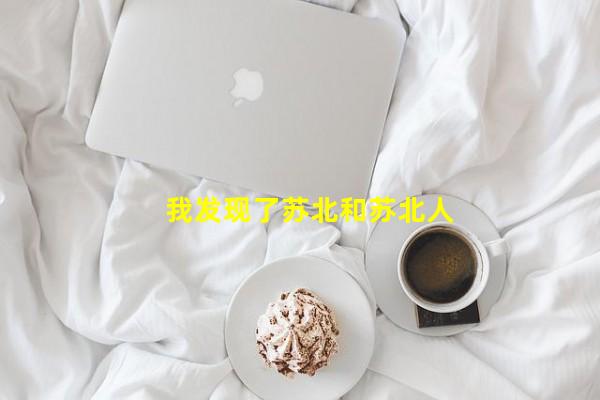
我一直喜欢电影《柳堡的故事》。
喜欢这部电影,是喜欢电影中出现的苏北乡间的风情,特别是两个主角,一个村姑和一个年青英俊的军人,腾腾的乡土气,跃跃的青春。
这种好感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我喜欢苏北的一大原因。
几十年过去,至今我还是喜欢苏北的风光,苏北的吃,苏北的人。
每有假日,总想去苏北,还去了两次苏北宝应,寻找拍摄电影时的外景场地,体验电影中的苏北风情。
电影叫《柳堡的故事》,外景场地真的是在一个叫柳堡的地方,在宝应治下。
两次去柳堡都是在十多年前,前次是春天,后次是秋天。
第一次去宝应,是开车从高邮沿着大运河237省道一直朝北,过了界首镇,就一路问过去,终于看到通往柳堡的路标。
柳堡在237省道东面,通往柳堡的道路是乡道,当时还是石子路。
已是四月天,沿路春柳拂风,白杨绽芽,两旁河塘已有荷尖出水——柳堡原来地处藕乡。
终于到了柳堡。
这是一个小集镇,和大多数苏北小镇一样,一条新街,两旁是各种小店。
看此情景,我有点意外,更多的是失望。
问乡人,都说这里是柳堡,没有第二个柳堡。
再问电影《柳堡的故事》,不是不知就是说不出所以然。
讲起“二妹子”,似乎还有印象。
我们吃了一碗苏北面,算是到此一游。
过了两三年,我又游苏北,又从高邮沿大运河走,又过了界首,看到去柳堡的路标,把车右转,再找“柳堡的故事”。
已是九月,路柳已成衰柳,只见装满白生生藕的车辆往外驶,时见路旁成堆的藕在过秤装车——已是丰收的时季。
到了柳堡,一干部模样的老人听说我们要找电影的拍摄现场,一脸喜悦,说:“你们真有心。
现场不在这里,在乡下,现在可以开车过去,那里还有当年的场景。
”那是继续向东的路,虽然已是村道,但仍很好走,两旁尽是无际的稻田和大小的池河,稻已泛黄,柳仍成行,果然是“种满柳树的村堡”,一派水乡风光。
路过桥边的油坊和抽水机房,走出一个中年人,指着脚下的河道说,当年拍电影的人就是在这里起岸的。
这是一条通外的河道,想必当年电影摄制组人员一定是经大运河,从宝应或高邮县城,经水路乘船到这里的。
过了桥,又过一程,见村头一家农舍敞着门,正在宰鸡杀鸭。
见不速之客,主人很是开心,说今天家有客来,正在准备中饭。
“你们问的当年拍电影的地方就在那边,看到有风车的地方就是。
”他说着走出宅屋围墙门,用手指方向。
我们下车,沿着田埂走去,到了桥头,又沿着河岸,河的两旁尽是黄灿灿的水稻,一架风车就在河岸,风中微动。
风车是否旧物已不重要,看着风车,我眼前浮起的只是春风中的二妹子和十八岁的哥哥,电影中的许多印记都已褪去,只留苏北的美好。
回到停车的地方,我们去那家人家道谢。
这家人家和村落不相连,四五间平房,红砖黑平瓦,外面打着围墙,全屋笼在绿树中。
未进墙门只闻鸡犬声,进门只见地上杂花,架上满是藤蔓,挂着丝瓜和扁豆。
主人家已开桌,人满桌。
见我们,主人喜出望外,留我们一起吃饭。
见我们推辞,女主人出屋,“嗤嗤”几声,从瓜藤上扯了五六只丝瓜给我们。
那是下部膨大、只只有二三斤重的秋丝瓜。
我们不知所措:这么大这么老的丝瓜能不能吃?见我们迟疑,女主人连说“好吃奈,好吃奈”。
我还以之前在柳堡集镇买的一包卤菜和一包油氽花生米,大家作别。
屋里的客人都出墙门来,像是在送别亲眷。
至今记得,那丝瓜远比上海的丝瓜好吃,肉乳白而嫩,不知是苏北地方种还是新品种。
后来在上海也见到过类似形状的丝瓜,买来吃过,只是那么大那么好吃的再也未见过。
最近,老友传来有关电影演员廖有梁的视频。
廖有梁在电影《柳堡的故事》里扮演“十八岁的哥哥”,我一直以为他是北方人,没想到他是上海嘉定人。
廖姓在嘉定是大姓,不知他和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嘉定人廖世承是否同宗。
看了视频,还想起了扮演二妹子的陶玉玲。
作为老观众,除了常想到他们当年给我们的“美的享受”外,我还想再去一次柳堡,看看那架风车,再去看看那家善良的苏北人家。
栏目主编:孔令君 文字编辑:孔令君 题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