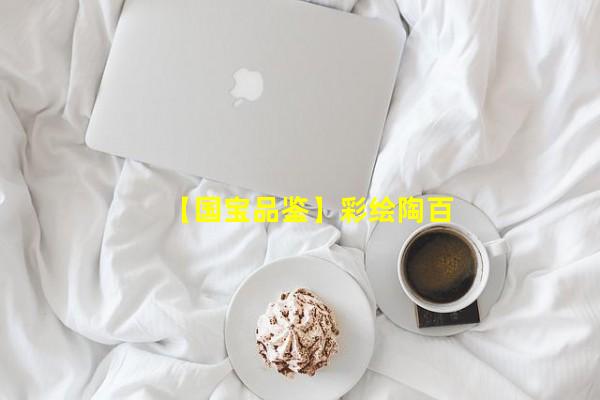
彩绘陶百花灯,陶质,东汉,陶器,通高92厘米。
1972年洛阳市涧西区东汉墓出土。
现藏洛阳博物馆。
彩绘陶百花灯这件彩绘陶百花灯整体分为灯盏、灯柱、灯座三部分。
最上部为灯盏,呈朱雀造型,朱雀头昂尾翘,双翅展开,头、尾和双翅将灯盏分为四等分,形如花瓣;中间部分为灯柱。
灯柱插接12支曲枝灯盏,分三层,每层4支,枝端承托灯盏。
曲枝接近灯柱部位分别端坐一羽人。
灯盏口沿有12叶柿蒂饰和8只卧蝉。
灯柱下端有一圆盘,盘沿上插有4支龙形饰,龙尾分别端坐一羽人。
灯柱下有乌龟承托整个灯柱;最下部为象征山峦的喇叭形灯座,座身自下而上分为3层,塑有猫、羊、狗、虎、鹿、猴等30多只动物形象。
这件百花灯通体彩绘,先以白粉做底,然后绘以红、黑等色,使得该灯显得非常华丽。
整件百花灯酷似一棵造型优美的古树,装饰效果很强,与汉画像砖中的扶桑树倒立图极为相似。
这件百花灯是汉代社会“长生不老”、“羽化升仙”思想的物化表现。
其灯座呈覆盆状,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仙山——昆仑山十分相似。
汉代志怪小说集《海内十洲记》这样描述昆仑山,“方广万里,形如覆盆”。
《尔雅》曰:“山三成为昆丘。
”也就是说,昆仑山是由三层组成的,这与灯座上的人物和动物呈三层排列的设计十分吻合。
据《神异经》记载:“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
”古人认为,天柱是顶天立地的象征,把天堂、人间和地狱联系到了一起。
百花灯的灯柱即代表昆仑山上的天柱。
百花灯上的十二枝曲枝形灯盏,分为三层插在灯柱上,形成了三层天盘,分别代表传说中昆仑山上的三座城池,同时,灯上所塑乌龟、羽人、龙、虎等都是古代象征长生和羽化升仙的神禽瑞兽。
这件百花灯是汉代艺术大师杰出的创造,反映了汉代精湛的制陶技艺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百花灯灯柱百花灯上的乘龙羽人百花灯底座扶桑树纹画像砖比较研究百花灯,又称“树形灯”、“多枝灯”、“连枝灯”,是中国古代灯具中最独特的灯具形制之一,它以树的形状为基本造型,多姿多彩、内涵丰富。
一般为一个灯座之上支撑高低错落几个至十多个灯盏。
由于其“灯盏”较多,犹如盛开的花朵,故称之为“百花灯”。
以枝状的数量来划分,有三枝灯、五枝灯、九枝灯、十枝灯、十三枝灯、十五枝灯等。
以“奇数”,即“阳数”的枝状最多。
山西大同北魏墓出土的漆画屏风中有三枝灯造型。
灯底为柱础形,座上为直筒形灯柱。
柱顶及左右曲枝上各有一灯盏。
云南黔西南州交乐汉墓出土一件五枝铜灯。
通高117.2厘米。
整灯由灯座、灯枝、灯盏三部分组成。
灯座由一玄武和两条龙盘绕而成。
玄武背负一赤裸曲膝顶灯人,灯柱从人头上伸出。
中央一枝塑一造型生动的龙,下面四枝则分别有人鸟造型。
湖南长沙五里牌出土一件七枝铜灯, 灯通高90厘米。
由灯座、灯柱、曲枝、灯盘构成。
灯柱分两节,每节伸出曲枝三枝,曲枝和柱端各托一圆形灯盘。
1964年,江苏徐州十里铺出土一件东汉九枝陶灯,该灯高53厘米。
灯座呈覆盆形,中心立灯柱。
从柱身分上、中、下三层交错伸出曲枝灯盏,曲枝端上层为羊首,中层为龙首,下层为虎首,兽首涂朱,额顶有安插灯盏的圆孔。
灯盏为浅园盘,盘底有短柄正好插入兽头额顶,取放十分方便。
十枝连枝灯见于广西贵港罗泊湾一号西汉墓。
通高85.2厘米。
十三枝灯以洛阳涧西东汉墓出土的这件彩绘陶百花灯为代表。
十五连枝灯以1977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连枝铜灯最为精美。
山西大同北魏墓屏风漆画中的三枝灯云南黔西南州交乐汉墓出土的连枝铜灯江苏徐州十里铺出土的东汉九枝陶灯广西贵港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西汉十枝铜灯连枝灯以铜质、陶质最为常见,还有少量铁质、瓷质。
铜连枝灯出现于在战国时期中晚期。
形体高大,大多在70~100厘米左右。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连枝铜灯,高84.5厘米,是战国中晚期出土的最高灯具。
整体造型犹如一棵大树,主干矗立在镂空夔龙纹底座上,由三只独首双身、口衔圆环的猛虎托起。
四周伸出七节树枝,枝上托起15盏灯盘。
全灯由大小八节接插而成,每节有榫铆,移动时便于安装和拆卸。
十五连枝铜灯装饰华丽、设计精致,制作工艺考究,灯盏错落有致,树枝上饰有游龙、鸣鸟、玩猴等,人、猴、鸟、龙共处一体,构思奇特,妙趣横生。
是我国古代青铜连枝灯具中的精品。
1993年,甘肃肃南汉墓出土一件汉代十三枝铜灯,通高80.5厘米,由灯座、灯柱和灯盏组成。
灯柱为圆柱体,呈竹节状,分为四段。
顶部是一碗形灯盏,中部分三层,每层各有一个四瓣花叶座,每个花叶座上饰四个龙形灯枝,各灯枝尾部也顶着碗形灯盏。
灯枝、灯盏及其装饰物均单独铸造,然后插接组合成为一体。
陶连枝灯出土数量最多,最著名的有三件。
除洛阳涧西东汉墓出土的这件彩绘百花灯外,另两件分别出土于河南济源泗涧沟汉墓和陕西宝鸡周原汉墓。
与铜连枝灯相比较,尽管陶百花灯没有铜连枝灯高大,但装饰显然要华丽繁杂的多。
且陶连枝灯一般将底座做成山峦形,堆塑一些仙人、神禽瑞兽等吉祥神性化的形象,使器物增添了浓厚的神话迷信色彩,寄寓着汉代人祈求永恒幸福,企慕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美好愿望。
铁连枝灯在战国已经出现。
张守义先生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过一件战国连枝铁灯。
该灯为五枝灯。
底座上树立一灯柱,灯柱中部分出四枝,枝端有一灯盏,灯柱顶端也有一灯盏。
洛阳烧沟汉墓M1035出土的汉代十三枝铁灯。
高73厘米,下部有一圆形底座,中间有一灯柱,沿柱向外分层伸出十二灯枝。
每枝枝头都有一圆形灯盏,加上灯柱顶上站立的瑞鸟,共十三枝。
瓷连枝灯很少见,目前见于报道的仅有四川乐山西坝窑出土的连枝瓷灯一例。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青铜十五枝灯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墓出土百花灯陕西宝鸡周原汉墓出土的朱雀陶灯战国连枝铁灯洛阳烧沟汉墓M1035出土铁百花灯四川乐山西坝窑连枝瓷灯从材料来看,铁连枝灯没有铜连枝灯贵重,且造型较为简单,制作相对粗糙,使用者得身份不高,似为平民或地位并不高的富户乡绅所用之物。
青铜在古代乃贵重之物,尤其是在商周时期非贵族不可使用,所以青铜灯具当为豪门贵族所有。
在造型和内涵上,铁连枝灯和铜连枝灯均比较简单,远不及陶百花灯精美,因此,在文化内涵上显然没有陶百花灯那么丰富。
这可能处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就工艺而言,陶器的可塑性远比铁器和铜器要强,古代制陶工艺发展到汉代已经处于巅峰状态,因此,陶百花灯更能体现出汉代高超的制陶工艺水平。
其二是设计精美、制作考究的陶百花灯可能是豪门贵族仿照生前所用的青铜连枝灯专门制作的随葬明器。
既然是专用的随葬明器,增加一些想象中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化元素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连枝灯的使用年代,学者大多认为,其出现于战国中晚期,流行于东汉,之后消失。
但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材料来看,似乎不限于战国至汉代这段历史时期,应该延续时间更长。
如唐李商隐《楚宫》诗:“如何一柱观,不碍九枝灯?”又唐温庭筠《晚坐寄友人》诗云:“九枝灯在琐窗空,希逸无聊恨不同。
”可见,唐代连枝灯仍在使用。
四川乐山西坝窑出土的连枝瓷灯上有“泰和重宝”款识。
“泰和”(1201~1208年)是金章宗完颜璟的第三个年号,说明这件连枝灯是金代之器物,将连枝灯的使用年代延长了上千年。
作者简介李胜军,河南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毕业,洛阳市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李萌,毕业于郑州大学会计学专业,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助理馆员。
着力于文物和博物馆学方面的研究。














